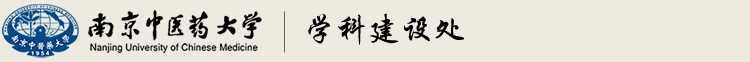高等教育评价是依据特定原则、标准及系列方法、举措对高等教育运行状态、性质、成效等作出判定、估价的系统性工程。一直以来,数字凭借其直观精准、便捷高效等特性成为高等教育评价中的主导性工具并被认为理所当然,这诱发了数字尺度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简单化运用并全方位挟持了高等教育的组织运作。无论外部评价抑或内部评价,高等教育评价都显示出鲜明的数字依附特征。
那么,到底何谓“依附”?审视依附理论中依附概念的学术流变可窥见其核心要义。依附理论最初仅限于探讨经济问题,所揭示的是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商业、金融、技术等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牵制状态。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明确指出:“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另一国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制约。”此后,依附理论由经济领域推广运用到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研究领域,其中在教育领域形成了高等教育依附理论。该理论旨在揭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因对发达国家教育模式、语言、知识生产、人员等过度依赖而受牵制的状态。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揭示出教育依附所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潘懋元等指出,依附,讲的是丧失自我意识,被动地学习。学者李均认为,依附不反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只反映主从关系,作为“从”的一方基本上没有“主体意识”或“主体意识”模糊,对“主”的一方的任何理论不加选择地吸收、照搬。从上述不同依附理论研究者的阐释中可以看出,依附所指涉的是因过度依赖而形成的一种牵制状态,其核心要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路径依赖,即依附者对主导者的某种工具价值过度依赖;二是结果牵制,即过度依赖导致依附者丧失主体意识而从属于主导者,并最终被主导者制约和控制。以此为鉴,本文提出“数字依附”概念。它是指高等教育评价主客体对数字工具乃至数字本身过度依赖,甚至将其升华为具有规训性质的“信仰”,从而被数字牵制的状态。具体而言,数字依附不仅指涉高等教育评价过度量化中对数字工具的高度依赖,还包含着数字尺度所具有的规训意涵。
需指出的是,数字作为一种评价性工具或符号,评价主客体对其认同与依赖本无可非议。但当数字化工具被推崇备至达到极端化程度而具有了规训性质时,高等教育场域中人的存在就被消解在抽象的数字集合之中,其功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被遮蔽,高校之间及内部无序竞争和学术生态失衡亦不断加剧。基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并对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的治理提出了制度性、政策性引导。为此,本文拟对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依附现象进行梳理剖析,以期提出消解之道。
一、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的现实表征
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依附是可以明确觉察的客观事实,这表现为数字符号运用于高等教育评价的各个向度与环节,数字尺度居于优先位置,成为判定高等教育质量、效率的核心符号,甚至被升华为无可置疑的“权力”。数字泛滥、数字优先、数字规训分别从数字运用的广度、深度以及性质上确证着数字依附,三者相互交织与渗透,构成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症候群的现实样态。
(一)数字泛滥:广泛渗透到高等教育评价的各个角落
当前,数字依附的直观体现是数字高频度与大面积介入高等教育评价全过程。这表现为其将评价对象分解为若干指标并赋予每项指标相应的数字化权重,进而再将单独的数字整合为系统化的数字集合体,构成综合评价高校的参照系。具体而言,数字尺度全面影响高等教育评价主要表现为从宏观评价到微观评价的层层介入。宏观而论,国家对高校的整体权威性综合评价表征为一串串数字或数字组合。“211”“985”等作为高度浓缩的数字标签,成为大学水平、社会地位的象征性符号。这种评价还进一步分解到高校整体运作的各个角度,亦被分解为更精准的数字。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所关涉的师资队伍、学生就业、科研立项、论文发表、奖项获取等无不对应换算成具体的数值。微观而论,在高度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下,关乎高校命运的数字触角延伸到二级学院并进一步介入高等教育运作基层中对教师与学生的评价。首先,重点学科数、特色专业数、重点研究基地数、重点实验室数、精品课程数、教学科研获奖数等数字指标成为衡量高校内部二级学院发展水平的根本依据。其次,数字指标任务进一步落实到评价基层教师和学生身上,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和学生学习生涯全过程。如教师从考核到职称评定,硬性评价指标普遍体现为论文篇数、科研立项数、课时量、获奖数等,更有甚者采用“工分制”对教师进行考核。对于学生而言,从入校到毕业的考核、评奖、评优各个环节,数字主导了其学习过程的各个向度,如德育分数、学业成绩、考勤得分、学习排名等。
概言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高校抑或是微观层面的学院以及教师和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被层层精细分解为数字,衍生出隐形的数字压力传导链条,数字符号由上至下渗透到高等教育评价的各个角落。更应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又进一步被整合为完善的数字体系,构筑成坚不可摧的数字集合体,衍射到高等教育评价的各个位置。大范围内高频度地运用数字测度高等教育质量,致使复杂而深刻的高等教育活动沦为精细化数字的集合。大学也由此陷入数字泥潭的危险境地,它赖以立身的理想、信念、精神等内在品质被抽象的数字符号所侵蚀,其工具化、庸俗化趋势不断加剧。
(二)数字优先:成为高等教育评价坐标系的优先尺度
尽管对于理性地运用多种尺度综合考量高等教育质量是评价的基本准则与普遍共识,但现实的高等教育评价在评价方式的选取上优先选择数字尺度却是有目共睹。具体而论,以数字为尺度的量化评价方式被置于优先地位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数字尺度的决定性。高等教育评价多依据数字尺度作出判断,有意无意地忽视数字以外的其他评判尺度。数字尺度既是高等教育评价的前提与依据,亦是高等教育评价恪守的标准,致使无论是可量化的评价对象,还是不可量化的评价对象都用数字施以计量,如学生思想品德评分、教师师德评分等。第二,数字尺度的不容变通性。为保障评价的“客观”与“公正”,评价者往往依据精准的数字指标实施“一刀切”式的评价,无任何灵活回旋的余地。以学术成果产出为例,高校明确将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毕业的硬性条件,将论文数、课时量、项目经费等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等,这已是司空见惯并被普遍接受的客观事实。
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尺度的合理运用无可厚非,但前提应是明确数字所承载的教育含金量。现实情况却是,数字指标所指称的丰富内涵被抽取掉而沦为方便管理排序的工具。此时,具有教育意义的其他评价尺度在数字尺度面前显得如此无力,处于自惭形秽的窘境。它们或者成为评价的点缀性存在,或者完全被悬置。至此,数字尺度在优先选择与运用中被推到评价前台。数字尺度将评价对象从所依存的文化场域中抽离出来,然后从理论上将其分解为不同的指标,并赋予这些指标一定数值。此时,丰富而深刻的高等教育活动便被分解为一个个机械的数字。可见,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优先实质上是用部分显性的数字指标代替对整体、内部的深入考察。这必然导致那些无法用数字指标反映的内在成分被遮蔽或遗忘,其结果便是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高等教育全貌。更为严峻的是,在数字尺度优先的评价体制下,高等教育运作愈益表层化,逐渐偏离对精神意志、文化品质、高深知识等深度价值的追求而诉诸外显、可测度的教育事项,高等教育的多元、丰富与深刻在数字优先的挤压下日渐变得扁平、空洞与肤浅。
(三)数字规训:异化为高等教育评价的规训力量
高等教育评价中理性的数字运用必然建立在对数字客观分析、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以有效调动评价对象的积极性,引导评价对象指向符合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自组织运作。但这种评价性数字一旦具有非理性特质并成为无处不在的力量,高校的教育选择与高等教育场域内的个体行为以其为转移,那么高等教育评价就会成为以数字为表征的新型客观化权力。与此同时,伴随着数字尺度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大面积与高频度运用,如果围绕评价对象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精细化的评价系统,那么数字化评价就会成为控制评价对象的规训技术,非理性数字就会无视高等教育灵魂中的自由、开放、创造等特质而畸变为具有规训性质的力量。此种外在的规训力量体现为高等教育评价场域中的数字至上。此时,复杂的高等教育评价沦为简单化计数工作,“数量取胜”跃升为第一生存法则,数字化指标成为指导评价对象的行为原则和终极追求。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人文品格与社会良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更应注意的是,评价对象在数字目标的挟持下逐渐丧失辨识力,放弃了高等教育的精神品格和社会责任并堆砌和制造各种数字。如当前高校场域内的学术不端现象,不得不说是部分大学教师在巨大科研压力之下为达到考核评价的数字目标铤而走险的后果。
应当申明的是,即便评价对象在理性上不愿为数字的力量所牵制,但数字的“权力”性质却又迫使其不得不伴着数字起舞。“个人一旦甘于接受别人用他们制定的标准来测量自己的个人成长,那么也就很快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自行测量。此时,个人已无须任何外在强制,便可自行进入他人指定的位置,不敢越雷池一步”。评价对象虽不满数字指标带来的巨大身体与精神压力,但又急于通过数字证明自己,做起“数字游戏”,甚至不惜“数字造假”。评价性数字“不仅仅是一个驱赶的鞭子,它还像是一个扣紧在机构与学术人颈部上的牵引绳,让大学与教师失去了自我掌控的方向感”。显然,此时的数字已然具有了非理性的特质,形塑成对评价对象的宰制性力量,数字标尺与评价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此时,大学不再是诗意栖居的求学问道之所,而沦为被抽象数字绑架的机械性社会组织。该场域内的个体亦丧失了批判审视意识,他们甘于接受数字指标的评估,成为各种数字性指标的依附性存在。由此,高等教育评价应然的激励与导向功能均出现较为严重的异化,这不仅与教育评价初衷相悖离,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等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二、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的成因探析
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依附实质上是把数字所承载的评价尺度作为高等教育评价的根本性尺度并使其由工具性存在转变成目的性存在,是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尺度的畸变。究其根源,数字依附是技术主义、简化主义、绩效主义等多要素汇流与交织的结果。
(一)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理性主义评价观长期制约
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活动,秉持何种评价理念是其根本。当前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背后的评价理念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理性主义评价观。该评价观承袭“世界可以由人的理性进行测度、控制和支配”的理性主义内核,主张用可量化的数字指标测度教育质量。其逻辑原点源自伽利略(Galileodi Vincenzo Bonaultide Galilei)的“质还原为量”观念,即“一切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事物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还原为量来加以处理,人们可以运用量的理性逻辑建构一切”。这种观念在现代被进一步放大,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提出的“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东西都可测量”著名论断,即是数量的理性逻辑在教育评价领域的生发与践行。当以数字工具量化的技术思维进入高等教育评价领域时,传统的定性评价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唯有以数字符号为主要表征的量化评价模式才是科学评价成为植根于评价主客体内心深处的信条。此时,数字远远溢出其应然的计数功能,被神化为高等教育评价中客观、标准、正当的象征而被优先选择和广泛使用。
回顾理性主义评价观统摄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评价的发展历程,它最初体现为传统考试结果量化,进而发展为科学主义支配下的教育测量,而后以泰勒(Ralph W. Tyler)“八年研究”(Eight-YearStudy)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评价方式成为里程碑之作。自此以后,在现代教育评价技术推动之下,高等教育评价逐步提高评价尺度的客观化与精准化,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尺度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描述的“数字化生存”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尺度在现实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的渗透。“‘数字化生存’不只描绘了一个被0和1两个数字所主宰的世界,更揭示了一种思维模式的变革,确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似乎都达成了共识:不以科学量化言说社会事件则不为科学,不以实证方法言说问题则不足以正确描述问题。”诚如舒尔曼(Lee S. Shulman)所言:“量化的方法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观。”作为量化标志性符号的数字已不单是一种评价工具,而是凭借客观、精确、标准等科学特性成为人类借以实现其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说,高等教育评价中对数字尺度的早期强调通过人类第三次科技浪潮时代场域的萃取,最终生发为数字依附评价理念并贯穿高等教育评价实践始终。至此,一种具有数字依附特质的理性主义评价观在高等教育场域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应当承认,理性主义评价观在历史上曾促成高等教育评价走向重数字的技术样态,推动了高等教育科学评价的发展。但是当理性主义评价观极致化为唯理性主义评价观,数字评价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凭借优势成为贯穿高等教育评价始终、渗透高等教育评价各层面的评价范式时,这不免导致评价主客体对数字的全方位依附。伴随唯理性主义评价范式弊端的逐步凸显,学界不乏反思的声音,例如学者们提出超越纯粹数字实证评价范式的阐释学评价范式。但是,当前高等教育评价中占据绝对主导并起支配作用的唯理性主义评价观远未打破,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依附依然根深蒂固。
(二)高等教育场域简单化认知的推波助澜
高等教育评价以高等教育质量的完整系统为评价对象。总体而论,高等教育质量既表征在显性场域的诸多指标上,亦存在于隐性场域的诸多维度上。在很大程度上,数字计量的意义取决于对高等教育场域整体性的把握与体认。而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完整样态我们应当将其置于高校这一特殊的社会场域之中加以考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指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任何组织都由两类相互依存的场域构成,即显性场域和隐性场域。对于高校社会组织,其显性场域是外在“物”的存在及相互关系,如由人、财、物等外显性存在构筑起来的物理性时空;隐性场域则体现为很难或不可能精确掌控的文化或精神空间。
审视现实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对评价对象的认知,由于缺乏对高等教育复杂要素及其关系内在广度与深度的把握,对高等教育场域的体认往往停留于显性场域上,而隐性场域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无视。导致这种状态源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宏大叙事式认识方式的局限。宏大叙事式的认识理路表现为评价主体在对高等教育场域做出认识并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依据粗线条、大时空、外显性等尺度。此时,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细节及隐于其背后的诸多关系被忽略,高等教育场域的外显层被置于前台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高等教育场域的全部。二是片面追求评价的可比性。高等教育评价的初心当是以评促教、以评促研,在鞭策后进、激励先进中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一初心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追求可比性成为评价的主旨,各类评价更多地在于实现排序功能。此时,高等教育场域中,其显性场域的诸要素及关系因具有更强的可计量性、易于排序而被突出;隐性场域因柔韧、模糊等不易昭示复杂系统的特质而被遮蔽。
高等教育隐性场域被遮蔽而退隐至高等教育评价视野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使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量化原则大行其道,佐证着数字尺度的正当性。如果说理性主义评价观从评价理念上确证了数字尺度的正当性,那么高等教育隐性场域的遮蔽则从评价对象上印证着数字尺度的合理性。于是,高等教育评价往往只关注具有可测度性的显性场域,并通过强化数字尺度的客观性、准确性、严谨性等特性而不断碾压其他评价尺度。此时,数字尺度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巩固并强化,获得了绝对权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优先地位并在高等教育评价中广泛使用。在相当程度上,对高等教育复杂系统的简单化认知,更确切地说对高等教育隐性场域的遮蔽,是导致当前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问题的一个深刻认识根源。
(三)数字得以彰显的资源黑洞与利益诱导
审视高等教育评价背后的理论假设,绩效主义占据了重要位置,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评价主客体的思想与行为。绩效主义“以绩效为核心,以层层分解指标任务为重点,以精细化的量化考核为杠杆,以经济奖励和惩罚为基本手段”,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于量化评估绩效并将评价结果与奖惩密切挂钩以激励评价对象。正是在绩效主义导向下,高等教育评价十分强调数字指标、结果排名等,并将以数字符号标示的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高度挂钩。此时,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化尺度与其承载的资源配置之间构成“表里”关系。高等教育评价表现出的高度数字依附只是外在表象,究其实质乃是根植于数字背后的资源配置机制。
首先,数字支配着物质资源配给。以统计数据为表征的评价结果构成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层级式资源配给模式。当前,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综合评价,还是学科评估、教学水平评估等单项评价,数字符号标示的评价结果都直接决定了高校获取资源的质与量。数据显示,“211工程”仅“九五”和“十五”两期建设的资金就高达368.26亿元,而三期“985工程”总投入资金更是高达904.76亿元。当利益链传导到评价终端,教师作为最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其绩效津贴的多寡直接取决于教学成果获奖、论文、著作、项目等指标的数据呈现,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更高的资源摄取。当前,教学科研奖励精致的数字标价已成常态,教师被裹挟其中而沦为追逐与数字指标挂钩的物质利益的“买卖人”。其次,数字意味着精神资源摄取。各类评价性数字不仅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主导性依据,亦成为教育水平与实力的指称物。在对高校进行各向度的评价中,数字符号事关学校声誉,意味着特定的精神资源摄取。当各类孤立的评价性数字被计算加总并获得相应的排名次序时,这样的评价结果就被即刻赋权成为一种身份符号和实力象征,它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大学的神经。这种评价机制亦通行于高校内部管理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中。论文、著作、课题等都被定格为特定数字,这些数字意味着职称、“帽子”、奖项,是教师个体化的学术声誉及学术资本的指称物。
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它们都是高等教育各环节及各组织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当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符号成为教育资源的标签并决定资源的结构性分配时,它们既可显示为组织运作现实绩效,亦是组织未来绩效获取的后续性、支持性条件。数字由此调控着高校的组织运作,驾驭着高等教育场域中每个人的生活。具体到办学主体——高校,各种评价性数字承载着的资金投入、声誉保障等渗透到学校运作的各个层次。此时,发生于高校之间及高校内部的各种数字竞赛“早已不是学校和学术共同体这个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而演变为学生、教师、学校、地方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生存竞争”。所以,评价对象对这些数字高度敏感与依附实属其强大资源操控力使然。另外,评价对象在数字巨大资源操控力全方位、持续性压制与诱导之下,组织意义上的内在自主性与个体意义上的理性判断力被销蚀殆尽。在各种数字指标面前,评价对象甚至失去了对数字进行审视与质疑的“觉悟”状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为了获取教育资源,他们给予各种评价性数字以深度的关注与投入,以致对这些数字本身的价值有无与高低选择麻木性遗忘,显示出在数字面前的自我渺小与自我迷失。概言之,数字的强大资源操控力所造成的评价对象的自我迷失亦是促成其对数字高度依附的根源之一。
三、消解高等教育评价数字依附的行动路向
消解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依附并非完全摒弃数字,而是要破除数字尺度运用的至上性与绝对性,以促使数字尺度在“唯”与“不唯”间取得平衡,这会触及对高等教育灵魂的深度领悟与现实高等教育实践中各利益主体搏弈的理性化引导。具体到操作实践,高等教育评价要实现数字依附顽疾的标本兼治,首要前提是还原评价性数字的本真意义,进而既需在微观层面规约数字的运用边界,亦需从宏观层面整体优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一)还原数字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本真意义
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依附实质上是作为评价工具的数字异化为评价目的。因此,治理数字依附问题并非在高等教育评价中机械地消解数字。理性的策略是让异化的数字归于本位,在数字的理性取舍中建立起数字与高等教育质量的意义联结点,让数字能真正反映高等教育质量,成为有意义的评价符号。
第一,高等教育评价要加强对数字符号评价意义的甄别并加以剔除。高等教育评价的功能在于从特定角度综合或单一地对实践及成效作出判定,其根本目标指向在于激活高等教育活力。判断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有无评价意义可依据如下标准。一是就数字本身而论,数字可否承载所评价尺度的丰富内涵。在高等教育评价中,为体现评价的所谓客观性与公平性,评价的计数模式愈益精致化。但数字指标再丰富、数字体系再精致,倘若数字不能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品质,这样的评价数字就难以做到完全真实可靠。以教学水平评估为例,生师比、硕博教师比、校舍面积、教学实验室数量、精品课程数量、教学成果获奖数量等系列数字勾勒出精致的数字化评价体系。但教学活动本质上是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实践活动,真正富有生命力、想象力的教学活动必然内蕴深刻的价值与情感意涵,这些显然无法通过上述的精致数字表征。在现行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诸如此类不能承载评价尺度丰富内涵的数字不一而足,如将发文量、论文影响因子、课题经费视为教师学术水平的象征,将分数、获奖数当成学生优劣的证明,如此等等。二是就其功能发挥而论,数字评价是否激发了高等教育场域的活力及促进了其有序运作。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的很多数字已异化为高等教育场域内无序、恶性竞争的诱发因素,从地域、高校之间人才的无序流动中可窥见此异化数字的影子。当前,拥有的人才称号教师数量被视为高水平师资队伍的标志,因而有些高校不惜斥巨额教育资源招揽各种有称号的人才。他们进入新的“科研现场”因受科研周期、学术环境、梯队支持等因素制约,在新的研究场域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学术责任。不可否认,上述数字能从特定角度触及高等教育质量的某些方面,但若是不能真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质性内涵,甚至诱发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无序运作,那此时的评价性数字便失去了其应然的评价功能,沦为无实质评价意义的数字符号。因此在高等教育评价中,依据如上标准甄别数字符号的评价意义并适当加以剔除当是治理数字依附的切实之举。
第二,高等教育评价应揭示并确证数字所承载的教育意义。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功能之所以发生畸变,其根源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所承载的实质性意义被遮蔽,从而沦为一种空洞的表象性符号。克服这种弊端可从如下角度着手。一是充分考虑数字评价的前提保障。高等教育目标和使命的多元化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测量和评价是一项复杂工程,用数字化指标解释高等教育质量需要若干前提条件,包括指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解释力、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数据来源的真实性等。所以,利用数字进行高等教育评价时,前提的正确极为必要。数字的来源与真实自不必说,数字对某项评价指标的解释力亦需得到确证。例如在学术评价中,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学术水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性这一前提应给予充分考量。简言之,文章数量与学术水平绝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即便是发表在同一级别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水平亦会表现出相应差异。此时,科学的评价应当回归到对如上前提的仔细推敲,从而使学术水平得到真实体现。二是明确数字符号在评价中的质性内涵。一般而论,数字在评价中总是在相应维度上指称一定的标准与内涵,而绝不仅仅是数量多少意义上的标示。在利用数字进行评价时,此标准与内涵应当进行深度阐释并明确。如此,简单的数字比较才会转化为有实质性意义的深度比较,数字化的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才会相互支撑与辅证,从而实现评价的公正与科学。三是加强各项数字融通的综合考量。高等教育评价应重点深化综合评价改革,建立捆绑式一体化评价制度,以打破数字指标的碎片化运用,揭示各数字之间的相关性。捆绑式评价不是对各维度指标的简单相加,其评价重点在考察不同维度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成效。以科研评价为例,高校可设立人才培养作用(科研活动引领学生科研行为情况)、教学服务(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情况)、社会贡献(科研成果服务政府决策、科研成果社会应用情况)等指标并赋予一定权重。此时,数字才会构成数字化体系,切实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与样态。如此,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才会显示实质的学术含金量,人们追求的数字化成果才会回归理性轨道,“五唯”之风才会在相应程度上得到扼制。
(二)明确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运用的合理边界
教育场域的各个侧面都有自身的性质展示尺度,数字并非能普适性地运用到高等教育场域整体时空之中。数字的单线性、浅显性与确证性必然不相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差异性,这决定了数字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运用边界。当数字超越自身的运用边界时,高等教育评价则显示出相应的数字依附。为此,高等教育评价要充分关照高等教育的复杂性,理性使用数字,确证数字运用的合理边界。
第一,高等教育评价要厘清数字运用的外部边界。数字的外部边界意指数字的运用范围。对于可计量的评价对象,数字标示有其价值;对于不可精确计量的评价对象,数字评价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必将大打折扣。可见,数字效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评价对象本身的特性。明确评价对象中哪些是可以用数字进行测度,哪些是不能抑或无须用数字测度,把握数字的运用范围是合理使用数字工具的关键。宏观而论,高等教育的外显层主要以“物”的方式存在,具有可计量性,能够用数字进行测度;高等教育的缄默层主要体现为大学的宗旨、信念、精神、境界等,不存在可量化的规定性,因而从本体论上看不能或很难用精准的数字施以评价。微观而论,对高校学生的评价,专业知识的学习成绩在相应程度上可用数字作为表征;价值观念、道德品质、情感体验、精神修养等具有内隐模糊特质,难以用精确数字施以评价。其他诸多方面亦然,如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学术品质等。所以,确定数字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运用范围,依据不同类型的评价对象以及评价对象本身不同维度的特质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机制极为关键。
第二,高等教育评价要把握数字运用的内部边界。数字的内部边界指涉数字使用程度的适切性,包括数字运用的比例、频率、强度等。数字运用一旦超过程度边界,评价过程正当性与结果准确性便会陷于不可操控的窘境。所以,即便是对于可计量的评价对象,若不加考量地高频率、高强度、精细化运用数字符号则会把评价异化为烦琐评价、表演性评价等无意义评价。基于此,在微观的高等教育评价中,确立数字运用的内部程度边界极为必要。具体到操作实践,我们应重点把控高等教育评价过程前端评价标准确定与后端评价结果使用两个关键环节中数字运用程度的适切性。首先,我们应淡化数量标准,突出质量贡献。质量保障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拒绝在单一指标或证据的基础上评价学生、项目,或者学校的表现状况。为此,我们在确定评价标准时要避免将数字尺度作为高等教育评价中直接、单一、绝对的判断依据,而是在将其作为重要参考的同时重点突出质量贡献导向。就对高校的总体评价而论,淡化毕业率、论文数、获奖数等数量标准,突出学校办学方向、特色、社会影响及声誉等是主要改革方向。从更微观的评价来看,我们可从下述两方面率先突破。一方面,在研究生毕业评定中弱化论文发表的硬性数量要求,建立论文数量标准的质量标准替代机制:高质量期刊论文对低质量期刊论文的单向替代,即经同行评审专家认定的高质量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可低于限额,而超过数量上限的期刊论文则不允许纳入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认定范围;高质量学位论文对期刊论文的单向替代,即学位论文若体现研究生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创造性成果,并在校外盲审中一次性通过且均为优秀的,则无须对其所发表的期刊论文成果进行认定,研究生可直接申请学位。另一方面,教师学术评价实行以量化指标为参考的代表作“盲审答辩”制。借鉴学位论文盲审的形式,高校可设立学科职称评定专家委员会,由教师提供有限数量且最能反映其学术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供专家匿名评审,通过外审后再组织教师进行集中答辩。如此,过度的数字依赖与崇拜可从源头上得以遏制。其次,我们要降低评价结果数据的物质利益捆绑负载。在提升教育经费与教师薪酬以保障学校有效运转和教师体面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应避免直接将评价结果数据与高额物质奖励线性、密切地挂钩。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回归并强化以精神嘉奖为主的激励方式,以提振评价结果数据的荣誉性。通过上述举措,评价性数字的“强度”和“效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三)结构性优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高等教育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散点式、表层化的改革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解数字依附有所助益,如职称评价中的代表作制度等。但如上举措仍是克服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的枝节性探索与尝试。所以,深入高等教育评价内部,整体优化高等教育评价结构以根本解决这一顽症当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高等教育评价要增强方法论与具体评价方法的契合度。高等教育评价方法论是依据高等教育的旨归与功能发挥而做出的指导原则性表达。高等教育的时代要求、理想品格、育人指向等都决定了其评价方法论的诸多指向,如方法论层次上的时代性指向、复杂性特质、民主性原则等。具体评价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应当与方法论指向相互呼应,形成相互契合的结构体。现实高等教育评价中的数字依附追求评价的精准、刚性、有序而忽略评价的人文尺度,这实质上是评价方法没有充分关照高等教育评价方法论原则的反映。解决此问题具体可从如下两点入手。一是洞察具体评价方法的方法论指向,审视极致量化评价中其方法论原则的缺憾。极致量化评价是一种极度精确、简化、刚性的片面评价,有悖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模糊性、复杂性、多样性的原则要求。二是补齐非量化评价方法短板并强化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相互检验。在明晰量化方法、质性方法各自适应域的基础上,高等教育评价要注重两者间的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以使两类评价方法的运用在总的方法论原则统摄下形成相互支持的结构体。如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单向度地运用量化评价方法无法反映教师的内在品质。为此,高校可通过档案袋评价、借助大数据评价技术为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档案袋,将反映教师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学术旨趣等情况的材料纳入其中,以便专家评审时综合参考。如此,评价中的数字化指向会得到理性审视,高度的数字依附则可渐为消解。
第二,高等教育评价要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任何评价都会落实为具体的评价指标并形成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高等教育评价亦然。对于现实高等教育评价而言,对数字的依附实质上表现为评价中可计量指标在全面纳入评价视野的同时,不可计量或者不可数字化计量的指标被排斥在评价视野之外,因而优化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为强化不可计量指标,以冲淡数字指标一统天下的格局。一是丰富评价指标,增加评价指标的数量。依据评价维度的丰富性与特定评价维度的特质,我们要丰富评价指标的“点”,加强反映高等教育灵魂的非数量化评价指标构建并纳入评价视野。在新的评价体系中我们要更多地考察立德树人、师德师风、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和国家贡献等应该强调但未强调、已经强调但尚未实施、已经实施但落实不够的方面。二是增加体现高等教育人文精神指向的评价指标权重。评价指标权重是决定评价结构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决定指标结构体系中主次指标的重要体现。增加体现高等教育人文精神指向中不可精确计量评价指标的权重意味着评价指涉高等教育场域的深层,如师德师风、组织生命力等高等教育隐性场域。功利化数字依附在这一过程中会得到相应扼制乃至消解。三是强化影响高等教育功能可持续发挥的评价指标体系建构。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及功能发挥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由于其基础性、内隐性等性质,与高等教育功能现实即时性发挥客观存在相应距离,但这些指标却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体现其未来性的重要因素。体现在对高校的评价中,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学科配置,培养学生未来贡献社会的潜质如社会责任感、终身学习意识、适应未来的知识迁移能力等高校应给予充分关注。此类指标因其不可精确计量的性质或因与可计量功能发挥的距离较远而被忽略,强化此类指标的有效关注与建构则会弱化评价中对数字尺度的依附。
四、结语
当前,“五唯”顽瘴痼疾是高等教育评价必须直面的实践难题,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引发了学者的理论审思和中央的高度关切,对其进行治理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性政策导向。深究之,“五唯”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极度片面、简化、刚性的评价,最直观的体现即是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至上以及无评价意义数字的泛滥,它直接诱发了高等教育评价的数字依附。诚然,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与质性评价机制尚未健全的双重境遇下,数字作为必不可少的评价工具,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理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本是评价工具的数字异化为主导性评价尺度并沦为具有“规训”性质的“意识形态”而促成数字依附,当高度的数字依附助长“五唯”之风时,对其作出审视回应以究其解决之道当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践行破“五唯”的切实之举。
为澄清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数字依附”的概念用以表征高等教育评价对数字工具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训隐忧,梳理剖析了高等教育评价中数字依附的现实表征及其根源,并从数字工具运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优化等维度提出数字依附的消解路向。但是,上述举措仍是基于数字本身、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局部治理”。应当注意的是,数字依附所映射的高等教育评价问题具有相当的顽固性与复杂性,问题的破解既需触及对高等教育评价本真价值的深层次追问,亦需高等教育评价生态乃至整个高等教育治理的系统变革。强化同行评价、代表作制度等质性评价的专业性与公信力,重塑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权威的社会信任,以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评价,变革大学的管理主义思维与逻辑等,当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22年1月刊
作者: 么加利(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